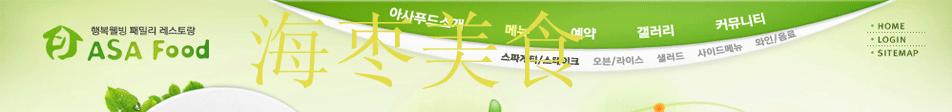|
北京白癜风手术费是多少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618910.html 在《史记》中,司马迁的人生是多姿多彩的,是自由浪漫的,又是坎坷曲折的,悲壮压抑的,遭遇不幸后更是极不自由的。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生,才考验了司马迁,锤炼了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恰似他人生所经历的晴天霹雳,最终将史官司马迁玉成了“文史祖宗”。在今天陕西省韩城市的“汉太史司马祠”里挂有司马后裔进献的牌匾,上面就题有“文史祖宗”,其义甚明:司马迁为中国文史之祖。无独有偶,近代学者柳诒徵先生也认为《史记》“为文学、历史两家之祖”。而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自然也是相近意义的评述。 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前,其实跟我们很多人并无多大的区别,他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有志青年,勤奋青年;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在参加工作后他也希望能够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点事情。在父亲去世前自己也并不非常明白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而父亲弥留之际的遗言让司马迁明白了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活着。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年),汉武帝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司马谈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这个伟大的文化盛事,所以心中满是愤懑,忧郁成疾,疾而成病,即将不久于人世。那么,司马谈为什么没能够参与封禅这样的汉朝天大的事呢?《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语曰:“武帝初,与诸儒议封事,命草其仪,及且封,尽罢诸儒不用,谈之滞周南,以罢不用之故也。”在这个时候,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所以,司马迁人生最重大的任务、人生最根本的意义就是要实现父亲的遗愿,那就是要完成一部“通古今之变”的史著。司马谈临终前所言:“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对这段许多学者耳熟能详的话,我们要认真深入分析。儿子能不能担任太史,这是司马谈决定不了的事情,前言“汝复为太史”,带有假设的成分,后言“余死,汝必为太史”,是临终之前的激愤之言,带有诅咒的成分,因为后面还说,如果你担任太史,那么不要忘记了我想要完成的那部论著。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在元封三年(公元前年),“卒三岁,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果真担任了太史令,“始为太史令,搜集史料”,当然这并不是说司马谈的诅咒起了作用,因为这个工作并非肥差,而且担任这个工作必须有一定的专业基础才可以,太史令之职相当于今天的专业技术人员,没有一定的积累和较高的专业素养是难以担任得了的,自然而然,长期受史学家风熏染的司马迁是最合适的人选。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后,牢记父亲的遗嘱,在父亲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档案文献的工作。“?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太史公自序》),?,《史记索隐》引如淳语,“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史记”为当时各国之“史记”,非今天之专名“史记”。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司马迁就开始了《史记》的撰述工作。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前年),当年汉武帝颁布太初历,改年号为太初。改历与封禅有着密切的联系,封禅象征新王朝受命于天;改历是封禅的继续,象征着受命的完成。“于是论次其文”,意为编次、定稿,一篇一篇地写定,这其实是他在父亲的成果基础上的继续,所以说《史记》是父子二人长达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正当他为这项工作做着积极准备,且已有了良好开始的同时,一个意外发生了,淳朴、单纯、踌躇满志的司马迁的人生因为这个事件而发生了惊天逆转,这就是遭李陵之祸。 到了第七年(前98年),司马迁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最终遭遇了宫刑。当时司马迁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于是就有了如下我们大家似曾相识的熟悉的一段名言: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 “《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之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以引起后来者的思考。” 说似曾相识,是因为这跟我们更熟悉的那段名言还有些不同,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会提到,兹不赘述。就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公允话、实在话,而且自己的初衷是为了解刘彻之困惑,纾解武帝之尴尬,然而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被刘彻打入牢狱,最终遭受了耻辱的宫刑!我们知道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但祸从天降的事却常常发生;这件事在司马迁的人生中,恰似大晴天爆炸的霹雳,让司马迁痛不欲生,差点轻生自杀,幸好最后还是隐忍“苟活”下来,但这件事也将一个普普通通的史官玉成了空前绝后的文史大师。 一、李陵事件之来龙去脉 关于李陵事件,《史记》《汉书》均有记载。《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陵在成年后,被选任为建章监,李陵善射,关爱士卒。天子认为李氏世世为将,让他负责管理八百骑。他曾经带兵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察地形,没有碰到敌人,平安归还。后来,李陵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天汉二年(前99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吸引匈奴兵力,确保汉武帝的大舅子李广利的胜利。“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 《汉书·李广苏建传》所记最详:天汉二年(前99年),贰师将军率三万骑兵出兵酒泉,在天山攻击匈奴右贤王。皇上召见李陵,想让他担任贰师将军的辎重运输任务,大概只是负责后勤管理的一般将官。李陵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在武台被召见,他对这件事有自己的想法,叩头自请说:“臣所率领的屯边士兵,都是荆楚的勇士奇材剑客,力大可扼虎,射箭能中目标,希望独立带领一队,到兰干山南去吸引单于的兵力,不让匈奴集中兵力攻击贰师将军。”这个说法也是合情合理的,自己是很有本事的人,打心底里不愿意做靠裙带关系当上将军的李广利的下属。汉武帝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说:“将军你讨厌做别人的下属吗?!哪里能拨给你人马呀!我派出了很多部队,已经没有骑兵派给你了。”李陵却回答说:“无须派骑兵,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就可以开进单于王庭。”这魄力实在是惊人,因为对于习惯了马上生活、马上作战的灵活机动性极强的匈奴人而言,步兵与之较量,自然是不占任何优势的。可即便是让他带着步兵,他也不愿做李广利的下属随从。汉武帝不好强求,也被他的勇猛打动了,便答应了李陵的请求。孤军深入,没有援军,自然是不可以的。于是汉武帝命令强弩都尉老将路博德率兵在途中迎接李陵军。路博德原是伏波将军,就像李陵耻于做李广利的后援一样,老将路博德也耻于做年轻将军李陵的后卫。路博德上奏说:“正当秋天匈奴马肥之际,不可与之交战,臣愿留李陵到春天,同时率酒泉、张掖骑兵各五千人,一起出击东西浚稽,一定可以擒获单于。”书奏上以后,皇上大怒,怀疑李陵后悔不想出兵,竟然而让路博德上书,这是二人沆瀣一气!如此一来,自己的大舅子便要孤军深入,怎么能确保获得出击的胜利呢?这还了得,臣子竟然不听我的,汉武帝便下诏对路博德说:“我想派给李陵骑兵,他说‘欲以少击众。’如今匈奴进入西河,我军应率兵奔西河,你要去钩营阻挡敌军。”又下诏对李陵说:“从九月出发,出兵遮虏鄣,到东浚稽山南龙勒水边,来回寻找匈奴,要是没有发现敌军,便从浞野侯赵破奴的旧路抵达受降城休整兵士,按骑兵驿站安排休整。与路博德讲了些什么话,全都写出来上报。” 李陵“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李陵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带兵长驱直入,士卒同心,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但猛虎架不住一群狼,李陵孤军深入,缺乏援兵,而匈奴倾全力围攻,形势岌岌可危,“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但在如此艰险的情形下,“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表现出了上下同心,共同御敌,不怕牺牲的可歌可泣的精神。在“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最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几乎全军覆没,不得不战败投降。这个消息传到后方朝廷,“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 李广利远征天山,天山即今之甘肃和青海之间的南祁连山,李陵出兵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西南部,路博德的出征路线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是“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钩营之道当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如此看来,这次出击匈奴分兵三路,互无接应,基本属于单打独斗。李陵最后全军覆没,投降匈奴,是因为老将路博德以为其后援而为耻,汉武帝于是让他出兵西河,使得李陵孤军奋战没有救援,这实际上是因汉武帝领导错误而导致的悲剧。 而李广利基本是个庸才,此次出征匈奴,汉武帝本想让他立功而获封,然而他带领着三万骑兵未遇匈奴主力,却打得大败而还。汉武帝见两路兵败,内心沮丧,颜面上过不去。于是,阿谀逢迎之臣下,都讳言贰师之败,全把责任推到了李陵身上。司马迁对朝中大臣耍两面派的做法很看不惯。当汉武帝召问时,“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意思是,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而司马迁与李陵并无深交,“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盃酒接殷勤之欢。”这完全是就事论事,秉持一颗公心,抱着为皇帝分忧解困的初衷来发表对李陵事件的看法的。司马迁说:“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意为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李陵带少数将士转战千里,且后无援兵,仍然杀伤近万敌军,司马迁认为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至于李陵力竭投降,司马迁以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还可能找机会主动报答国家的……”,“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汉书?司马迁传》)“久之,上悔陵无救”,汉武帝派遣“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汉书?李广苏建传》) “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按照汉朝刑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的人若想不死,有两种减免的办法,或是用50万钱赎罪,或是实行宫刑,破坏生殖器官。由于没有钱财,为了能够活下去,他只好选择了“宫刑”。天汉二年,司马迁被关进监狱,天汉三年,在“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的消息后,汉武帝“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这样,司马迁为李陵所做的大胆辩护也就暂时失败,于是“下迁腐刑”。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据李将军、匈奴列传及汉书武帝纪、李陵传,陵降匈奴,在天汉二年。盖史公以二年下吏,至三年尚在缧绁,其受刑亦当在三年而不在二年也。”郑鹤声先生认为王说极是。 什么叫宫刑呢?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这些不同的名称都反映出这一刑罚的残酷。一般人在受宫刑以后,因创口极易感染中风,若要苟全一命,须留在似蚕室一般的密室中,在不见风与阳光的环境里待上百日,创口才能愈合。宫刑又称腐刑,这是因为,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从此像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结实,故名。 宫刑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尚书》中有多处提到了“五刑”和“宫刑”,《尧典》中就有“五刑有服”语。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字为会意字,由“士”与“寸”二字构成。在古代,“士”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士女”即男女;“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与“寸”合在一起就是用刀割去男性生殖器。男子受宫刑,一般理解是将阴茎连根割去,但据古籍记载,也有破坏阴囊与睾丸者。《韵会》一书云:“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外肾是指阴囊和睾丸,破坏了它,人的性腺即不再发育,阴茎不能勃起,从而丧失了性能力。 遭李陵之祸,被迫接受了宫刑,这对司马迁的影响极为严重。遭受宫刑后,司马迁一直沉浸在耻辱之中,心情极为痛苦。他在《报任安书》里说:自己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为什么如此痛苦呢?除了身体残缺的原因,还有精神方面的原因。因为宫刑最初的作用是为了惩罚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即“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丈夫淫,割其势也”。受宫刑者,起初皆为淫乱者;后来,此刑也施之于某些非淫乱者,但仍以淫乱者为主。司马迁是以非淫乱者受的宫刑。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淫乱是大恶、大耻,“万恶淫为首”,因此法制上便采取了极为残忍的割去生殖器的刑罚。司马迁并没有犯淫乱罪,只是发表了使汉武帝不快的言论,却被施以原本是用来惩罚淫乱者的“淫刑”;而且,宫刑用的是骟马阉猪式的方法,是用整治牲口的办法整治人,此刑可谓“兽刑”;再者,受宫刑意味着跟宦官相类,而宦官是一群有人格缺陷和道德缺陷的人,是一群被世人看不起,并视之为丑类的人。司马迁非常鄙视宦官,在《报任安书》里,他特别说到自古以来人们就以做宦官为耻,并列举了孔子因为曾由宦官陪同出游而感到耻辱等例子。但如今自己恰恰因为受了宫刑而与宦官有了相同之处,这一切都使得他深深感受到了莫大的耻辱。而且从五刑的排列顺序来看,五刑分为奴隶制五刑和封建制五刑,奴隶制五刑分为墨、劓、刖、宫、大辟。宫刑是肉刑中最重的,仅次于大辟(斩首),显然,当时人们的思想中还残留着原始时代的初民对生殖器崇拜的影响,生殖器的价值仅次于头颅。 当然,遭受宫刑之所以给司马迁带来巨大的耻辱,除了以上几个原因外,从司马迁自身来说,是因为他的知耻观念特别强。司马迁的思想体系主要是儒家的,他是孔子的崇拜者,孔子及其弟子与后学所创立的儒家,是极讲“耻”的观念的。孔子说,“行己有耻”,“有耻且格”,“知耻近乎勇”,把“耻”作为立身行事的重要准则。所以,司马迁的知耻观念特别强,是深受了儒家的影响的。因之,他的《报任安书》通篇都贯穿着儒家的“耻”的观念,贯穿着“知耻近乎勇”的因耻辱而发愤的精神。 二、李陵事件之意义 当然,司马迁被处以宫刑,习惯上称为“遭李陵之祸”。事实上,李陵的“投降”,背后反映的是李氏家族与汉武帝及外戚集团之间的长期、复杂的矛盾,“李陵之祸的真正原因,是李陵家族与汉武帝及其外戚集团之间的长期私人恩怨所致。然后由此牵连到司马迁,并卷入其中,酿成遭受宫刑的祸端。”因为汉武帝宠幸卫子夫,引起了陈阿娇及其母亲长公主刘嫖的不满,于是长公主囚禁了卫青,欲置卫青于死地,卫青在其好兄弟公孙敖等人的帮助下,才侥幸保住了性命。后来公孙敖因故失侯,卫青在出击匈奴时为保证公孙敖立功,将本为前将军的李广并入右将军赵食其部,结果李广因迷路失期而最终自杀。后来,李广的儿子李敢报复卫青,击伤了卫青,霍去病为给舅舅出气,竟然射杀了李敢。汉武帝不能公正执法,袒护霍去病,竟然公然说谎,说李敢是被鹿“触杀”的。 李陵“投降”之后,汉武帝也同情李陵的战败投降是因为没有援兵,所以派公孙敖深入匈奴迎接李陵回汉。结果,“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汉书·李广苏建传》)公孙敖官不大,与李氏家族的悲剧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李陵派人刺杀李绪的事,是司马迁死后才揭晓的事,因而《史记》中未能记载。从《汉书》记载来看,汉武帝在李陵投降匈奴一年多后,曾派公孙敖率兵深入匈奴腹地,迎接李陵归来,但公孙敖无功而还,向汉武帝报告撒谎说李陵在帮助单于练兵,防备汉军,所以我才无功而还。汉武帝听了,于是诛杀了李陵全家。在《汉书》中,只是客观地叙述了公孙敖编造谎言,误杀李陵一家的历史真实。”因为汉武帝的偏袒外家,导致了李氏家族的悲剧,同时也导致了司马迁的悲剧,“败降匈奴一事改变了李陵的一生,使他从此在孤寂痛苦的渊薮中终其一生;而因着为李陵言致下腐刑一事,也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的确如此,自此后,原来循规蹈矩、恪尽职守、奉法循理的史官司马迁死掉了,一个高瞻远瞩、犀利睿智、沉郁激愤、多愁善感的司马迁诞生了。他有着无比的自信和超乎常人的坚强,坚信自己能够成功,他见惯了世态的炎凉,漠视了别人的冷言冷语;他勇于坚持,十年磨一剑,像苏秦一样头悬梁、锥刺股,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让他及他的父亲乃至司马家族青史留名,名传千古。因了《史记》这部书,司马迁成为了中国古代少有的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愚蠢的人和智慧的人、一般人和有成就的人都会经历坎坷和失败,人生都会经历失去,但他们的不同在于智慧的人能从失败中获得经验和奋起的力量,能够正确看待得失,一次的失去往往能够换来更大的收获。 我们每个人不一定会有司马迁一样的遭遇,但是每个人的一生都不会一帆风顺,一帆风顺的人生也注定难以品尝到幸福的滋味。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成功的故事各不相同,但任何一个成功人士的成功秘诀中除了机遇,更缺少不了“坚持”这两个字。古语说得好,“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万事开头难,一个开头已经将很多人拦在了成功大门的外边,开始后坚持下来的又少之又少,真正最后成功的人就是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也许一次并不一定就能成功,但是坚持到最后即使失败了也是一种成功,因为这一次的失败为下一次的、最后的成功积累了经验。 “五福”中第一福是寿,最后一福是“考终命”,即善终,就是要享尽天年。人要生活得幸福,离开得安详。人大概是世间所有生物中对生死最为敏感的一类。人们往往自诩是高级、理性的动物,但实际上,作为万灵之长的人在驾驭万物的同时,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就是,要面临死亡的恐惧和威胁。在司马迁时代,他接受了宫刑,隐忍苟活下来,并不是说明司马迁怕死,其实,他并不怕死,在《史记》众多人物传记中有许许多多的面临生死抉择的例子,司马迁赞美了一些人的勇敢决绝的死,那是“重于泰山”,也肯定了一些人的隐忍苟活。如果不能死得光荣,那就坚持活下来,活下来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事。在某种意义上说,活是比死更为痛苦、更为坚强的事情。 司马迁坚持活了下来,他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存在的价值,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存在的人生价值不该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自己不应因遭受了耻辱之刑就自寻短见。在《季布栾布列传》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对生死问题作了较详细深入的说明:“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意思是,以项羽那种豪气干云的气概,季布却靠勇敢在楚地扬名,他亲身消灭敌军,多次拔取敌人军旗,可算得上是好汉了。然而他遭受刑罚,给人做奴仆不肯死去,显得多么卑下啊!但他这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自负有才能,不甘心如此毫无意义地死去,这才蒙受屈辱而不以为羞耻,以期发挥他未曾施展的才干,所以终于成了汉朝的名将。这不正是司马迁在为自己接受宫刑而“苟活”在做辩护吗?!自己如果死去,自己的才干同样无法施展,更无从完成父亲的遗嘱了。贤能的人真正能够看重他的死,至于奴婢、姬妾这些低贱的人因为感愤而自杀的,算不得勇敢,那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一死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栾布痛哭彭越,把赴汤镬就死看得如同回家一样,他真正晓得要死得其所,而不是吝惜自己的生命。即使古代重义轻生的人,又怎么能超过他呢! 正如司马迁所言,死亡并不可怕,死亡并不困难,关键是怎样对待死,怎样死才有意义,才更有价值。这才是司马迁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