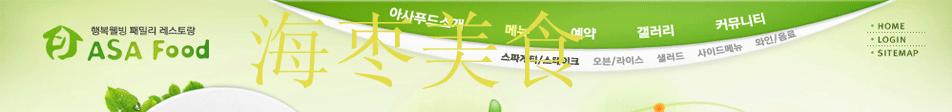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吴天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新闻记者、电视编导、诗人作家,现供职于中国海关。创作的长诗《攀登者》获《诗刊》优秀作品提名奖、《因为无法忘却》获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和平勋章》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山河望》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先后出版诗集《策马向西》、《铁血红》、《山河望》、《时光指针》、《光阴契约》;散文集《灵魂掌灯》;报告文学集《和平勋章》、《铁血金魂》等。 匈奴遗响 作者 吴天鹏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 绝人之材,淹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 ──龚自珍 火车如同一张紧绷的弓背,轰鸣着越过黄河,将一座座巨兽般的浑黄山包甩在了身后,缓缓地驶进古浪峡口。这就是当年匈奴依凭东拒大汉的天然屏障,峡侧峰岭上依稀可见的秦汉长城烽燧,似乎在向我展示着两千多年前那一场场如月弯刀掀起的战争狂飙。 浑黄的土山包倏忽掠过车窗,遥望远处,祁连山峰顶上的冰雪依然如一条横亘的银龙,自苍宇间游动而来。河西走廊在片片葱碧的绿树沃野间,如同一片流光溢彩的锦帛进入了我的眼帘。这就是位于黄河之西,又夹处在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脉与蒙古高原之间的一条长约多公里,宽数十至数百公里的河西走廊。它曾是中原通往西域最重要的通道,也是曾诞生和养育匈奴先祖的圣地。无数次聆听过关于匈奴的故事,也无法理清这道业已消失的血脉中到底孕育了多少英武悲壮,让我们先把目光拉回到那个遥远的岁月深处,去倾听这个沉入历史长河的民族遗响吧。 那是遥远的夏商时代,一位名叫淳维的王子,因父王的错误决断,被族人逐出了中原。王子怀着对故乡的眷恋和族人的仇恨,开始了漫长岁月的放逐。从此,辽阔的大漠上有了缕缕炊烟,有了被他们驯服的牛羊和野马。他们追逐着朝阳暮霞,靠盘马弯弓射猎为食,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从阴山脚下远涉寒冷的西伯利亚,穿越荒凉的天山北麓。在穿越了沙尘漫天的蒙古大漠之后,终于发现了草肥水丰的河西走廊。并在此修筑王庭,建立疆域。用剽悍不羁的坚强建立了休屠王城,形成了北方一个强大的民族。自此,河西走廊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始端。 史书对匈奴人是这样描述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岁正月诸王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笼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带林,课校人畜计。其法拔刃者死,坐盗者不入其家。有罪,小则轧,大则死。狱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 王子的后裔们,快乐地在这片水草肥美的草原上生息繁衍,他们把南面那如同一个巨大屏风的山脉拜为天赐之山(祁连是古匈奴语天的意思),山上消融的雪水滋润着这片肥沃的土地,古浪峡口以其无比峻险隔断了东眺不远的中原。千余年后,一个被中原人称之为“戎”或“匈奴”的民族在这里崛起了。广阔的蒙古草原,肥沃的辽东黑土,凡他们祖先流浪过的地方,都成了他们的领土。这个马背上生存、河西走廊养育的欧亚第一个游牧民族用剽悍向世人展示匈奴铁骑摧锋挫锷般的狂飙战风。 摊开历史闪耀着灿烂辉光的绵延长卷,那些远去的背影或模糊或清晰,都成了岁月堆积的厚度,经一次又一次战乱的砥砺,一个民族必将变得更加坚强,也必将拥有凛然的风骨和英武的精神之气。 虽然我们更清晰地追寻到匈奴是在汉武帝建立的大汉王朝,其实匈奴的名字在战国时期就已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一个部族。自西汉以来,中国古代文籍记述匈奴先民即殷周鬼方、猃狁。也有西来、北来等说。匈奴无文字,以语言为约束。留传至今的少量古代汉语文有甚少记录。就匈奴语汇与氏族名,难于对其族属与语族作出准确判断,目前主要有突厥、蒙古等说。匈奴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的最初活动中心地区,为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见于记载的匈奴第一个单于,驻头曼城。(当今内蒙古包头市境内)。战国末叶,匈奴与东胡并强,常扰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郡,三国相继筑长城以拒匈奴与东胡;秦始皇复使蒙恬统30万众连成万里长城。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统万城,是世界上发现的惟一的匈奴都城遗址。随着它在沉睡千年之后浮出沙海,才使蒙在这个消失的民族头顶上的疑团得以揭开。站在这个巍峨的城墩之下,手抚如石头一般坚固的城墙,人们不禁会问:这沙漫墙头的古城难道就是匈奴的遗响,在中国北方驰骋了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的匈奴哪里去了? 我总是觉得,匈奴从中华版图上消失,是一种巨大的遗憾。这种遗憾就像一块无法愈合的伤口,虽然久远但还能感觉到一种隐隐的疼痛。在甘肃山丹路易艾黎博物馆,收藏着两件匈奴人的遗物:一柄弯刀,一支鸣镝,见证着匈奴民族的刚猛雄悍。我不知道这柄弯刀曾经握在那位匈奴的手中,并用它砍杀了多少颗大汉兵卒的头颅,喷涌的鲜血淹没了多少拔节的青草。但一身红锈的弯刀,至今观之仍觉心生惊惧。我也不知道那枝鸣镝是否是冒顿单于用以射杀父亲头曼的那一枝,但从历史的云烟深处隐透出的那种骨肉相戕的残忍,虽穿越千年时光,至今让人心生寒意。 公元前年,冒顿杀其父头曼,废单于推举制度,自立为单于。从此,匈奴遂由族名,兼为单于国名。公元前~前年,冒顿在位,掌控兵将30余万,吞并楼烦、白羊王、东胡、月氏、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族。老上单于继冒顿之后,又从伊犁河流域驱逐月氏、乌孙徙居伊犁河流域,于是匈奴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北部草原游牧各部中,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游牧军事政权。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焉支山像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点缀在文字纵密的典籍当中。自老上单于击败月氏王国后,在多年的匈奴历史上,焉支山一直是匈奴重要的生存基地和军事屏障,有赖于祁连山与焉支山的丰美牧场,匈奴民族才得以强盛起来,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匈奴的军事扩张对西汉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决不会坐视一待,由此发大军征剿被视为“夷狄”的匈奴人。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年)秋,匈奴军南下攻山西晋阳。第二年,刘邦亲率步兵三十二万,从晋阳北上迎击。刘邦见匈奴败退,遂产生一种一举消灭匈奴的念头。匈奴首领冒顿闻知刘邦的狂傲,为引诱汉军北上,把善战的兵丁和骠肥体壮的马匹都隐蔽起来,汉军看到的尽是瘦弱的人畜。轻敌的刘邦率骑兵穿越雁门关到达平城,在抵达白登山时,大批的步兵还远在后方。冒顿见时机已到,遂及遣精骑四十万将白登山团团包围。刘邦被困七日,粮草不济,人马困顿。万般无奈的刘邦用陈平的秘计,派人贿赂匈奴的皇后阏氏,才仓皇逃离白登山与大军回合,引兵而归。 白登一战,使这个马背上建立中原大汉王朝的皇帝尝到了匈奴铁骑的威猛剽悍,也从中吸取了教训。由此下决心建立强大的骑兵,鼓励民众私分养马。民间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的景象,朝廷养马也达四五十万匹。 匈奴狂飙般的铁蹄声,曾经是一种历史的旋律。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年)春季,汉武帝命令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上万精骑,长途奔袭匈奴军。霍去病从陇西出发向西挺进,以势如破竹之速,先后经过5个小国,所到之地纷纷兵败,差一点捉住单于的儿子。霍去病大军越过甘肃省山丹县南的焉支山,向西挺进千余里,与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部队遭遇,双方展开了惨烈的血肉搏杀,汉军大获全胜。俘获了浑邪王的儿子、相国、都尉和休屠王的祭天金人。 这是一首悲凉的古歌: 忘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女儿无颜色; 夺我金神人,使我不得祭于天。 这首歌的作者已无史可考,但它诞生的年代,也许就是汉武帝发动的那次毁灭性的战争时期。 焉支山作为匈奴的生存基地和军事屏障,在它身上发生的战争极为惨烈。但在西汉之初,匈奴人从未有过败绩,尤其在雁门、云中等地的战争,都是以汉王朝的失败告终。直到公元前年,西汉王朝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之后,觉得再也不能容忍匈奴对它的轻视和威胁,于是,便有了汉将王恢导演的“马邑之谋”。马邑伏击,汉军无功而返,汉武帝非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把消灭匈奴作为自己创造辉煌帝业的最高目标。四年之后的冬天,汉武帝又命卫青率大军出征匈奴,未过狼山,即遭惨败。这时的匈奴,以祁连、焉支为依托,越过渭水,浩荡大军势如破竹,接连攻克了汉朝的陇西、秦州等地。 公元前年,年仅23岁的霍去病率兵西征,一直深入到焉支山以西余里,大败匈奴,俘获匈奴名王以下数十人。同年,霍去病再度出击,还是在焉支山,攻破了匈奴的前线阵营,长驱直入,一直把匈奴驱赶到了敦煌以西的沙漠地带。至今,我们仍可以在山丹、张掖、酒泉等地看到许多汉、匈战争的遗迹。而焉支山的丧失,使匈奴从此一蹶不振,此后的百余年间,再也无力夺回自己丢失的家园。 在焉支山与汉王朝的数次战争中,匈奴损失了30多万兵勇和民众,牛羊万头。这对于一个游牧民族来说,是一种比什么都沉重的打击。然而匈奴并非因为失败而悲伤,他们真正的悲伤却是对故土的留恋和热爱。是祁连山和焉支山,强壮了他们民族的体魄,造就了他们纯真、强悍的民族性格。
而越过千年的时光,祁连山和焉支山上再也找不到他们曾经的足迹,鲜血早已化作了青草,遗骨成了茂盛的树木。一个有声有色的民族最终无声无息地消失,这与岁月的更替是那么地相似。站在焉支山上,我不知道那些西迁的匈奴,在黑海西岸,会不会翘首东望?黄沙白雪,高山流水都显得微不足道,而焉支和祁连,始终是匈奴心中一种永恒的疼痛和梦魇。 当到了吕后篡位夺权的时候,已是有些寂寞的冒顿却又突发奇想,写一封恣意戏弄和羞辱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的信,遣使臣送给了未央宫中指挥所有大汉男人的吕雉∶
“孤愤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孤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语言轻薄,竟是要娶这位新寡而权极一时的吕后为妻,两国共治,这对泱泱大汉是何等的轻蔑,这对那些一直尊孔孟之教而治国的汉君人臣是何等的侮辱啊!我想此后两千多年,凡汉室志士一直把早已湮灭了千余载的匈奴民族视为永久仇敌,与此事可能不无关联。
吕后接信后大怒,立即召陈平及樊哙、季布等大臣议斩其来使,发兵进击。樊哙当场请命说:“臣愿得精兵十万,横行于匈奴之中”而季布却对吕后说:“应该把这个吹牛的樊哙斩首,才几年前汉兵三十二万,樊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白登山,樊哙不能解围救高帝于水火,使天下百姓唱出了:‘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弯弩。’今歌谣之声犹闻于耳,伤病者还没有痊愈,而樊哙却扬言以十万兵击败匈奴,这是当面在欺骗你呀!”季布一番话说得樊哙汗渐无言,吕后默默点头。这位以强悍而著名的女皇不无屈辱的亲笔给冒顿写了这样一封回信,并派最高级别的使臣张泽亲自给冒顿送去: “单于不忘敝邑,赐之以书,敝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淤,敝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 也只有冒顿这样的伟人世奇男,才可能令吕后这样的女人写下如此屈辱的回信。这段史实,千百年来一直压抑得华夏文人志士难以忘却,又怎能不令那些历朝历代的忠臣们切齿呢?就连一千三百多年后,南宋的民族英雄岳飞不也是要“渴饮匈奴血”吗! 经过三四个朝代的革兵息马,大汉王朝已是马肥南山,仓禀充实了,可是大汉王朝以女色易苟安也已是近七十余载了。汉武帝这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年天子,登基伊始,就用他那充满仇恨的目光注视起北方那个令他祖先蒙辱的民族:“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汉武帝建元二年秋,长安上林苑建章宫中,目送着又一批艳丽的汉家宗室女,在凄泣声中被匈奴使者带走,年轻的汉武帝刘彻再也不能忍受这自大汉创基以来就订下的屈辱之盟,一剑望案几砍去:“自此之后,再有言和亲者斩!”此后近三百年里,两个原本同根的民族为了统治者的尊严,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 从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自元光二年,汉武帝遣韩安国、李广、卫青等首领首次出击匈奴的近十年大战中,战场基本上是在辽东上谷及河套地区展开的,双方大小战斗近百起,各有胜负。大汉王朝集七十余载的国力,虽将秦将蒙括得而复失的河套地区抢回,却又丢失了上谷造阳等地,一直到公元前年,十三载出使西域的张骞归汉,才使战争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机。 公元前年冬,度安驿的快马给在未央宫里的汉武帝及文武百官们带来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13年前出使西域邀月氏共击打匈奴的使臣张骞归来了。 当张骞颤栗地登上殿堂时,汉武帝早携文武百官出迎,望着这久违了的大汉宫门,望着已入中年更具威仪的武帝刘彻,张骞轰然伏地,膝行数丈,泣而奏道:“陛下,臣有辱使命,出使西域十载有三,跋千山涉万水,两度被匈奴拘囚,几经丧生。陛下赐千金百人随我出使,今匹马单人而还。臣于匈奴处不能死节,于月氏有辱使命,十三载劳而无功,请陛下治罪。”武帝亲手将张骞扶起,接过那杆已磨得只剩劲节的、代表着大汉皇帝威仪的汉节,望着这个十三年前如同雄师一般而现今虬须苍发的张骞,武帝感动了:“十三载匪囚,九死一生,汝今能持节以归,当何罪之有?” 武帝挽着张骞的手,登堂入殿。大殿内,张骞陈述了月氏国不敢出兵的缘由后,将一捆详细记载河西走廊地形的羊皮呈了上去,并奏曰:“臣虽不能说服月氏出兵,但十载被囚,困居河西,却将整个河西地图绘好,将这个天堂之地献给陛下!”接着,张骞详细地为武帝讲述了他在河西走廊的所见所闻:从雄伟壮观的茏城休屠王城到匈奴族人图腾的神灵──祭天金人。从那辽阔的绿州盛产的源源不断供给蒙古战场的粮食,到西域诸国通往这里的繁荣的贸易……“陛下,欲联西域,必通河西;欲固长安,必占河西;欲破匈奴,必得河西呀!” 无疑,是张骞的归汉,是张骞的一番哲理,才使得武帝如梦初醒。此时那一张详尽的河西走廊地图,在武帝看来犹如一片片飞来的捷报。霍去病两战定河西,河西走廊的丢失,使匈奴王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维系着整个蒙古草原铁骑将士们的粮食基地被毁灭了。又适逢大旱,百日无雨,茫茫的大漠荒原到处是一片片渴饿倒地的牛羊,整个国家经济猝然崩溃。祁连山下,居延河畔,到处涌动着向塞外迁徙的匈奴,伴唱着阵阵悲歌。 这年深秋,河西走廊西部的首领混邪王在重重压力下,无力再战,诱杀了不愿投降的休屠王,虏获了他的阏氏及太子,在凄凉的胡笳,呜咽的羌笛声中,向大汉王朝投诚了。至此,整个漠南再无王庭,河西走廊这块宝地从此进入了华夏大汉的版图.汉武帝在河西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以此为基地,连同西域诸国,向流亡在北漠草原上的匈奴发动了一次次毁灭性的打击。 匈奴毕竟是一个有数千年根基的剽悍民族。汉武帝在他五十三年皇帝生涯中,举倾国之兵,选绝世帅才,打了四十六年的战争,终是没能亲眼看到这个令他祖先蒙辱的民族消失。这个逞尽文韬武略的大汉皇帝在他有生之年,虽然尽夺失地,侵吞河西,但当瞑目之时,他的大汉王朝也随着他几十年的穷兵黩武而渐入民变土崩之中了。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失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失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不听李斯之劝,使蒙恬攻匈奴,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发天下男丁,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载,死者不可胜数,而天下男子疾耕不足以粮饷,女子纺织不足以帷幕,百姓靡敝,孤老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叛秦之始也”。 冒顿初立时,即爆发秦末农民起义,继之五年楚汉战争,匈奴南下夺秦九原郡(今包头及河套地区),与汉朝分界于河南塞(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势力达到朝那(今甘肃平凉市)、肤地(今陕西榆林县)。以后经历高后至文、景60余年间,匈奴贵族屡屡背约骚扰汉朝边那郡,屠戮吏民,掳掠人畜,汉朝仅防御处之。直至武帝经过两次带决定性的战役,匈奴大败,单于及左贤王亦皆通走,河西走廊平定。匈奴主部不得不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 失去了根据地的匈奴人,还顽强的守着北漠最后一片领地,并时不时的试图出击河西。以至在汉武帝去世的五十多年后,于元帝时期,双方又立下了和亲之盟,著名的王昭君出塞,就是在这个年代发生的,这是双方共同的利益需求,他们各自吮吸着残酷的战争给他们创下的难以愈合的伤口。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一度十分强盛的匈奴,在中国北方、中亚乃至欧洲各地不断地进行争战、迁居、再争战、再迁居,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居民的混杂、通婚和民族融合,作为民族的匈奴在公元6世纪后基本消失,渐渐交融到其他民族肌体之中。一个民族融入其他民族的进程是很快的。关于匈奴族的迁徙,中国史书除其内迁和滞留草原有较详记载外,对匈奴的西迁语焉不详,而欧洲学者则多有涉猎。公元前一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 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很可能留了下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 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一个民族的形成必将在交融、分合、更替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公元5世纪时,就在北匈奴阿提拉在欧洲建立起匈奴帝国,南匈奴几乎同时在中国建起帝国,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向定居文明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在战败后匈奴人便融入到其他民族之中了。可以说,这个伟大的民族至今也没有消失,它的血液还在当代其他民族的身上澎湃着。匈奴作为一个民族消失了,但其文化习俗仍部分保留下来了。以现在主要流行于蒙古国、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内蒙古与新疆的“胡笳”为例,胡笳虽为匈奴乐器,但其传播、继承却早已超出了匈奴。 公元前57年,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和内讧,5单于争立,内部大乱,陷于绝境。后来由于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在位(公元前58~前31),附汉为藩臣,汉朝待以殊礼,位居诸侯王之上,且以大量物资提供提供匈奴赈灾。于是汉与匈奴结为一家,关市大开,至王莽檀政以前,60余年和平发展,汉、匈人民都得以安定,出现了民众富庶,牛马布野的局面。匈奴单于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西汉末年及王莽篡位时期,王莽采取侮辱匈奴单于的政策,破坏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相安发展的汉匈关系,至东汉光武时始得到改变。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驻牧于匈奴之南、管领南边八部之众的蔜鞯日逐王比归附汉朝,自立为呼韩邪单于,于是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 北匈奴不仅常攻扰南单于,且屡掠汉边郡,侵迫西域诸国,阻塞中西交通。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东汉朝廷利用北匈奴内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混乱,社会危机十分深刻的时机,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军事出击。在汉将和南单于的联军合击下,连年大破北匈奴于大漠南北及今新疆东部,北单于受创遁逃,于永元三年率领一部分部众西迁。匈奴政权全部瓦解,残留在漠北的一部分匈奴余众,有十余万户加入了鲜卑;另有一部分始终留在漠北的西北角,直至5世纪初才被柔然吞并。残留在今新疆的匈奴余众则在那里继续活动了60多年。 南匈奴自入塞内附之后,受到汉朝的优厚待遇。和平、安定的环境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时,南匈奴人从入塞开始,不仅分布边缘诸郡,而且与汉人错居。《晋书?北狄匈奴传》说:“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就是指东汉的南匈奴人而言。与汉人杂居的以及分布缘边诸郡的南匈奴人,朝夕与汉人共同生活,或经常与汉人交往接触,自然受到汉人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经过40年左右,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及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时间可以忽略,这个堆积并垫厚史册的民族必将让我们去怀念和铭记。顺着历史的血脉,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个强盛而伟大的民族之脉。匈奴远去了,消失在遥远的风尘中了,但当我翻阅发黄的史册,顺着这个民族从诞生到辉煌直至消失的脉络,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来自血脉深处的力量使远去的匈奴似乎就和我近在咫尺,望着如今那些依然快乐地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我才真正懂得了那句:人类就是在文明和野蛮相互碰撞中发展起来的哲理,也许就是对消失的匈奴最好的诠释。 更多精彩文章: ■贾平凹:金钱可以使人卑微,却无法使人高贵 ■深度:我们离真正的文明还有多远? ■谢冕:海子之后,诗太容易写了,口语泛滥,误入歧途 ■余秋雨前期散文大气,后来作品粗制滥造较多 ■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钱理群:读懂“他妈的”,才能读懂鲁迅 来稿须知 本平台旨在“不厚名家、不薄新人,唯质取稿”。欢迎广大文字爱好者投稿。要求: 1.原创首发散文、小说、评论、诗歌3首以上编辑在一个word文档用附件形式发送邮箱: q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