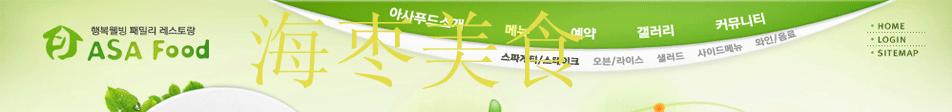|
近日读完高尔泰的《寻找家园》,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写一篇书评。几次想要下笔,几次都觉得不妥,不仅因为它带给我的触动太强烈,太原始,也因为面对这样一本书,任何评论性的语言都显得苍白多余。踟蹰下去似乎又要不了了之,终于下了狠心,一定要写点什么,无论如何,要推荐一下这本书。 这是一本散文集,也是一部回忆录。作者高尔泰老先生是著名画家、作家、美学家,曾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职,先后在兰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执教,现以学者身份旅居美国。 看似光鲜的职业履历之外,是一份触目惊心的个人履历:生于年,除了战乱,二十世纪中国所有的灾难都经历过,刚工作没几年就被打成右派,遣送夹边沟劳教农场,好不容易死里逃生,文革时又成了“牛鬼蛇神”,牛棚住过,五七干校也待过。“平反”之后,在大学任教,又几次被停课,被驱逐,八十年代末,还无缘无故被抓进牢里关了小半年。出来时女儿得了精神分裂症,妻子一度病危。 全书分成三卷,“梦里家山”、“流沙堕简”与“天苍地茫”,大致对应少年,青年与中老年。沉甸甸的四百多页,是一部苦难史,也是一部个人心灵史。 高尔泰生在江苏高淳,侵华战争以前,家境不算很优渥,但也富足,父亲学识渊博,家中有一楼藏书,还建过仓库,办过学,认识不少文化界的名人。高淳沦陷后,一家人逃难到大游山脚下,在一栋孤零零的茅屋里住下。 高尔泰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生活虽清苦,但远离兵燹,一家人在一起,也温馨平静。对孩子来说,乡野之中的隐居生活还有许多乐趣,林木茂密,泉水甘甜,还有无数山果野味。山脚下的村庄里保留着各色民俗,大刀会、摆香市、请鬼神,能遇见许多奇妙的人,道士、秀才、跳大神的“马甲”……父亲依照战前办学的经验,开办了一所小学,周围村庄里的孩子们都来读书,高尔泰的两个姐姐也在小学教书。他自己除了上学之外,只需要放放羊,剩下的时间都用来玩耍、画画。 晚年漂泊异乡,想起一切坎坷之前,那个一尘不染的童年,他写到,“我有时不免要想,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我们是过分地幸运了,后来的遭遇,就算是一种补课吧?” 第一次裁剪 那段在自由和平静中无忧无虑成长的时光,无形中塑造了高尔泰的性格。他形容自己是“一头野生动物”。他也确实“野”,有一股不管不顾的“虎”劲儿,生在意识形态的笼头勒得最紧的年代,他先天不能适应,后天也不肯被驯服。一生中几次遭难,又几次死里逃生,都跟这天性中的“野”有关。生死一发,系于偶然,福兮祸兮,已经说不清。 说到底,这“野”不过是一种叫做“个性”的东西,不过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愿意被磨去棱角,不甘心被统一剪裁,被当成奴隶和工具随意使用,不过是面对密不透风的牢笼,为了不完全窒息,而不得不做出的反叛。 解放之后,高尔泰一家迁回高淳,他在山里自由惯了,不适应城里学校的规矩,整天逃学,一再留级。最终决定出去学画,先去了丹阳的“正则艺专”,又到江苏师范学院。那时全国一盘棋,所有美术学院的教学方法都是苏联来的,力求画得像,画得真,排斥个性和想象力。高尔泰不喜欢,不想学了,要转系,犟了一阵,然而时局动荡,家回不去,老师同学又轮番来劝,做思想工作,终于硬着头皮走上了艺术的“正路”。 艺术上“正确”了,思想上还是“正确”不起来。年,高尔泰二十岁,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兰州郊区一个学校里教书,生活单调乏味,找不到意义,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受一群不相干的人的摆布,为什么受了摆布,不仅不能拒绝,还要快乐地感恩戴德地接受,久之形成了一种对于权力的憎恨。 极度憋闷之下,写作成了精神上唯一的出口,他花了一年时间,写了《论美》,驳斥当时以马列和唯物主义为主导的美学,写得很畅快。发表后引发了一场美学界的大争论,当时还是“大鸣大放”时期,标榜所谓的言论自由,然而不久之后,反右爆发,《论美》成了高尔泰最大的罪状,他成了学校里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 二十一岁那年,他踏上一辆西去的火车,来到了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劳教农场。 入死又出死 我第一次知道夹边沟,是在高中,一位关系不错的老师送给我一套杨显惠的纪实文学三部曲,其中有一本《夹边沟记事》。书中那些闻所未闻的悲惨情状,读后那种干冷窒塞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 夹边沟的恐怖,不亚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只不过一个是赤裸裸地屠杀,一个是打着“教化改造”的名义行屠杀之实。无止境的强制劳动,逼迫人们互相迫害、揭发,动辄辱骂殴打,后来饥荒爆发,极度饥饿之下,连吃死人的事情都时有发生,很多人病死饿死了,尸骨就扔在农场外的沙梁下面,那些年兰新铁路从远处通过,列车上的旅客经常闻到阵阵恶臭,都不知来自何处。 高尔泰在夹边沟待了一年多,饥荒爆发之前,他被抽调去兰州为“十年建设成就展”画画,死里逃生。回想在夹边沟的生活,除了劳动,有许多时间是坐着度过的,收了工,一群人坐在昏暗的死寂中,不敢说话,也无话可说。那种沉默取消了灵魂,把一切都变成了冷硬的物质: 坐着坐着,脑中没了思想。我生平第一次,发现了时间的硬度。时间作为我的生命的要素,或者我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变成了我的对立面,像一堵石砌的大墙,用它的阴冷、潮湿、滑溜溜的沉重,紧紧地抵着我的鼻尖,我的额头和我的胸膛。 在描写夹边沟的数篇文章中,有一篇《沙枣》,写一次劳动期间他偷偷溜走去摘沙枣充饥的经历,透着一种凄冷的诗意,我印象最深。劳动是在巴丹吉林沙漠与大戈壁之间大片的盐碱地上挖排碱沟。戈壁滩和盐碱地上不长别的植物,只长沙枣,这种果子小而涩,因为含碱,吃多了容易口渴,但能充饥。高尔泰趁收工时偷偷跑去摘,四周都是空旷的荒原,数百公里之内杳无人烟,逃跑就是死路一条,因此摘完还要迅速回来,赶上大部队。他回来时却迷了路,在黯淡的月光中焦急地寻找,终于看到排碱沟边堆土的痕迹: 新挖的排碱沟中,一泓积水映着天光,时而幽暗,时而晶亮,像一根颤动的琴弦,刚劲而柔和。沿着它行进,我像一头孤狼。想到在集体中听任摆布,我早已没了自我,而此刻,居然能自己掌握自己,忽然有一份感动,一种惊奇,一丝幸福的感觉掠过心头。像琴弦上跳出几个音符,一阵叮叮咚咚,复又无迹可求。 拥有了自我,也就拥有了世界。这种与世界的同一,不就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梦想着的自由吗? 月冷龙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荒漠之中,只有死和比死更凄凉的东西。自由是什么?只能是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个隐秘的向度,像精神病人偶尔的清醒,在难以预料的时刻出现,刚撑起一角坍塌的自我,又要回到牢笼。 高尔泰离开夹边沟之后,又在夹河滩农场待了几年,到了六二年,终于解除劳教,可以自谋出路。继续上学读书是不可能了,也没有反叛的道路,只盼望能找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安静度日,然而公社化全民皆兵的时代,哪有无人的角落?想来想去,想到了敦煌莫高窟。他想,或许可以像席勒一样逃进古典艺术的港湾中去,便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写了封信,毛遂自荐,谈对敦煌艺术的看法。本不抱希望,没想到对方看过他的信后,又调阅他的档案,看了他之前的文章,决定用他。 曾经置他于死地的,如今又让他绝处逢生。 在敦煌的头三年,是高尔泰青年时期难得的平静时光。面对洞窟中沉默千年的诸天神佛,尘世的喧嚣苦难仿佛黄粱一梦。然而时间久了,那空无寂静之中朦胧的彼岸,又浮现出另一些凄恻的东西。 他受不了,又一次逃进写作中去,偷偷地写,写人的价值,写人的异化和复归,写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写美是自由的象征。这样无边无际的诚实的写作,在当时非常危险,但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如果不通过书写,将自己与时代,与人类的历史联系起来,就会感到仿佛要被活埋一般,彻底地湮灭消失,不复存在了。 人间处处是囚笼 平静只持续了三年,好像浩劫与浩劫之间故意留下一个喘息的档口,让人休养生息,只为了承受更残酷的折磨。即使远在沙漠深处,只要有人存在,桃源就只能是个朦胧的梦想。文物所里的员工一共四十九个人,加上家属,整个敦煌不过百十来号人,但灾难一点也不比外面少。高尔泰是极右分子,首当其冲挨整,但其他人也没有好下场,今天整人的人明天就成了被整的人,最高峰时,四十九个人里二十几个都关进了牛棚。 文革中的种种事,家中长辈偶尔谈起,与书中记述相差无几。昔日的同事朋友一夜之间变成仇敌、开批斗会、戴高帽、红卫兵抄家;同是革命群众,分成两派互相斗,都宣称自己更忠于毛主席;“牛鬼蛇神”人人喊打,常常被打得浑身是血满地爬,打人的都是他们曾经最信任、最爱护的人…… 有一件事倒是敦煌独有的。唯物主义的天空下,敦煌的宗教文化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留着就得“消毒”。怎么个消毒法呢?革命群众把许多纤维板裁成报纸大小,订上边框漆成红色,再在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挂到洞子门上,就算“消毒”了。洞窟数百,工作量极大,还不是随便挂的,要有针对性,比方针对有饲虎图的洞窟,要挂“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那段,针对五百强盗成佛图,选了“看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有某个外星文明,无意中观测到了那个时期的中国,他们会如何评价这个文明?如何评价人类?他们能理解那些荒诞与矛盾并不是人性的常态吗?能理解那些狰狞的笑,欢乐的围殴,悚然的寂静,在夜色里跳个没完的忠字舞,黑暗里手电光下一闪一闪的鲜血,都是为了什么吗? 我想不能。连我们人类自己都不能。高尔泰也不能。八十年代“尘埃落定”之后,他去拜访过一些过去的同事朋友,许多人深受曾经深受文革之苦,常常被打得披头散发血流满面,甚至比他的亲身经历还凄惨许多,伤疤刚刚褪去,又恢复了信仰,又一次选择了“正确”。他理解不了,觉得对方正确得可怕,正确得令人毛骨悚然。 寻找家园 家里长辈总说,有些事情不堪想,想不通的,非要想通就活不下去了。也许这话是对的。在那个年代,似乎越是有骨气,越是真诚,越是想要脚踏实地生活的人,命运越悲惨。越想活得像个人,越被深深踩进泥土里。 当年抗战结束,回到家乡,高尔泰的父亲耗时几年,在物资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一砖一瓦,辛辛苦苦攒来材料,亲手重建了被战火摧毁的家宅。新屋三间两层,坚固美观。中庭挂一幅《岁朝清供图》,画两边对联上联“梅花绕屋香成海”,下联“修竹排云绿过墙”,字画都装了镜框,十分典雅。然而只住了一年。因为新屋修得漂亮,高尔泰家的成分被改为地主,新屋被没收,后来文革期间,高尔泰的父亲因为“地主”的身份被虐打致死,房子几十年后也没能收回来。 数十年来,多少人祸,最后都沦为了历史中的自然。不然又当如何?一次又一次运动里死了多少人?其中有多少知识分子,多少学者、艺术家、科学家,如果他们不死,能为社会做多少贡献?能推动多少精神和文明的发展?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肝肠寸断的家庭,无声无息地湮灭了,这笔账找谁算去?只能令往事如烟散。 八三年的“清污”运动,高尔泰因为几篇谈到异化现象的文章受到批判,被兰州大学停课,也不让发表文章、出书。几个月后运动又莫名中断了,他要求校党委道歉,不然拒不复课。最后离开兰大,先后到四川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任职,八九年突然被捕入狱,毫无缘由,小半年之后放出,也没有一句解释。九三年,高尔泰和妻子离开大陆,到美国定居。 寻找家园,家园何在?移居海外多年之后,高尔泰在序言中写: 奴隶没有祖国,我早已无分天涯……那些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生态,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命运,曾使我经常有一种在敌国作俘虏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超高温下凝固,超低温下冻结,干硬如铁,支撑着我们的脊梁和膝盖,使我们得以在非人的处境中活得稍微像个人。但是像个人样,也就是同非人的处境的疏离。 有人说我出国前后,文风判若两人,从激烈到平淡,表明叛逆者经由漂泊,学会了宽容与妥协。这是误解。宽容妥协是强者的特权,弱者如我辈,一无所有,不是可以学得来的。是在无穷的漂泊中所体验到的无穷尽的无力感、疏离感,或者说异乡人感(也都和混沌无序有关),让我涤除了许多历史的亢奋,学会了比较冷静的观看和书写。 回首往事,血腥污泥深处,碑碣沉沉。然而世外也无桃源,只有无尽漂泊。徘徊六合无相知,飘若浮云且西去。 读完这本书,已经是深夜。孤灯寂寥,也感到一种仿佛将被活埋的恐惧。想起以前读《夹边沟记事》,也失眠,苦闷中会想,为什么好好的要读这样的书?不是徒增烦恼吗?过去已经无法改变,为什么不能就让它这样过去? 如今已经不会再有这样的疑问,只对这些书的作者感到无比感激。感谢他们告诉我们,所谓“历史走了一段弯路”,背后是无数支离破碎的人生。感谢他们坚持相信,人不是手段,人是目的。这个简单的信念让高尔泰倒霉了一辈子,但也正是这个信念让他保全了自我,在深渊之中,没有损失自己的人性。 人不是手段,人是目的。人不可以随意被牺牲,随意被利用,随意成为“试验品”,或者“代价”,或者任何抽象概念的附庸,不管这个概念是种族还是教派,是民族还是国家。人不可以轻易被湮灭,被遗忘。人有存在的权利,有追求自由的权利,有拥有个性的权利。 人生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只能根植于个体,根植于活生生的人。没有个体,就没有家园。正因如此,应该对一切打着集体,打着超越个人的抽象名号的东西有所警惕。 除此之外,我想,哪怕不能理解,哪怕“不堪想”,哪怕知道一件事发生过不一定能阻止同样的事再次发生,记忆也是一种责任,是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责任,此刻对过去的责任,历史对生命的责任,是我们,作为个体,对人性的责任。 那片浸透了血与泪的厚土,正是我们脚下的土地。 作家、画家高尔泰与妻子画家浦小雨 书评/影评/随笔/诗歌 瞎写写,图个开心 欢迎来瞎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