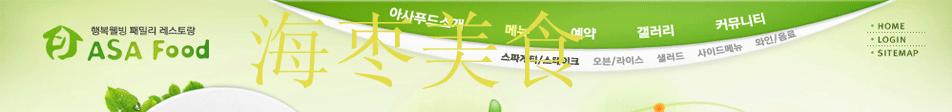|
北京什么医院治白癜风治的最好 http://m.39.net/pf/a_4323025.html 甘肃是古丝绸之路重要孔道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通道,自古以来就是古代中原与西域、东方和西方之间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核心区域和重要舞台。日前开幕的“丝路孔道——甘肃文物菁华展”以时间为轴,以文化交流为线索,以考古发掘的甘肃各历史时期的件(套)不同门类的重要文物为基础,呈现甘肃历史文化。 此次展览是历年来甘肃省在国内举办的文物展览中文物数量最多、珍贵文物占比最高的一次展览,是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观众全方位展示厚重多元、异彩纷呈的甘肃古代历史文化的一次大型文物展览,下面就让我们提前感受一下甘肃不同时期出土文物的魅力吧。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1、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一进展区,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件在《国家宝藏》第二季中,吴磊守护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该展品于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距今已经有年的历史。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局部) 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上千件陶器中,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是唯一一件塑有人像的彩陶瓶。为细泥红陶质地,圆鼓腹,平底。瓶高32.3厘米,口4厘米,底径6.8厘米,细泥红陶质地,绘有黑彩纹饰。瓶口呈圆雕的人头像,短发齐额,五官端正,挺鼻小嘴,面庞秀丽。眼和嘴都雕成孔洞,两耳各有一小穿孔,可以垂系饰物。五官镂空造成的深色阴影,成为头像富有表现力的因素。陶瓶的腹部绘有三条大致相同的黑彩画,主题花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两个弧边三角纹对接组成圆圈,内填充垂弧纹和弧纹;另一部分以斜直线、侧弧及凹边三角纹组成,图案呈二方连续。 这件人头瓶塑造了一位端庄、典雅、古朴、大方的美女形象,把人头与葫芦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情趣生动,体现出远古先民对自身力量的初步认识和艺术再现的能力。从制作手法上看,这件彩陶瓶上的圆雕人头像已运用了雕镂、贴塑、刻画等不同的雕塑手法。瓶身图案的韵律节奏及对称均衡的形式美,不仅显示出当时的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也浓缩了先民的审美意识及其丰富的社会内涵。 鲵鱼纹彩陶瓶 2、鲵鱼纹彩陶瓶 彩陶鲵鱼纹瓶年甘肃省甘谷县西坪遗址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仰韶文化器物。 这件鲵鱼纹彩陶瓶的纹饰为人面鱼身,双目圆睁,炯炯有神,张牙舞爪,呼之欲出,四肢弯曲,尾部尖细,躯体健硕,形象生动。其典雅的器型,精美的图案,让观者无不赞叹。躯体满绘的网格纹规整饱满,有了鲜明的几何图形特征。有学者认为鲵鱼纹是对娃娃鱼的真实描绘,表现的是一种自然的物象;有的认为其实关于这件彩陶瓶上的动物形象,考古界也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纹案就是娃娃鱼的真实图案;还有学者分析图案是人首蛇身,可能是伏羲氏的形象;还有人认为是龙的原始图形,鲵鱼的脸似人形,两眼有神,身躯卷曲,所以他们认为这种人面鲵鱼应该是中国最早的龙图。但不论是何形象,这件彩陶都让人们充分领略了彩陶的无穷魅力和幽远意境。 鲵鱼纹彩陶瓶(局部) 3、彩绘木轺车 彩绘木轺车,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磨嘴子汉墓,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彩绘木轺车 彩绘木轺车,马高88.2厘米、长78.8厘米;车高95.2厘米、长96.5厘米;御奴高33.6厘米。这组彩绘木轺车包括车、马、御奴共三件。车包括车舆、轮、辕、槽、伞盖等部分。舆车有双辕,车舆与车轮用黑白二色彩绘,出土时车轮尚能转动,各有16根辐条,完好无损。马用红、白、黑三色彩绘,头部有铜当卢、兽面饰衔嚼一副,颈上套轭。马头、颈、身、四肢和耳、尾都是分别制作,再用榫卯接合或粘连的方式组合而成。马头上双耳高竖,目若悬铃,挺胸扬尾。御奴跪坐于左侧,作双手持缰状,以黑、白两色勾出眼、鼻及冠服。伞盖顶部装盖斗,插16根弯曲的竹弓,上绷皂缯成圆形盖顶。 彩绘木轺车(局部) 这组彩绘铜饰木轺车结构复杂、形制壮观,是汉代出土的同类器物中既完整又规模大的一组,制作精细,形象逼真,装饰豪华,车舆形制复杂,雕工精巧。车的轻便简洁与马的雄伟健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汉代木雕作品,也是现存汉代木轺车马保存较完好的一件。它真实地反映了汉代河西走廊生活富足、文化发达的社会面貌,为研究汉代的舆服制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考古史料。 “白马作”毛笔 4、“白马作”毛笔 年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磨嘴子49号汉墓出土了一支毛笔,笔上落款为“白马作”,这支毛笔是迄今我国所有出土汉笔中保存最完整、制作最精良、最早刻有笔工姓名而闻名国内外的一支。“白马作”毛笔被专家公认为是我国汉代毛笔的代表作,被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白马作”毛笔(局部) 毛笔通长23.5厘米,这正是汉制长度单位的一尺,笔杆长21.9厘米,竹质,精细匀正。笔杆中下部阴刻隶书“白马作”三字。“白马”当为制作此笔的工匠名,说明当时仍保存“物勤工名”的手工业传统。笔杆包笔头略有收分,笔头长1.6厘米,外覆较软的黄褐色毛,笔芯及笔锋用较硬的紫黑色毛,刚柔相济,富有弹性,体现了笔头中含长毫,有芯有锋,外披短毛,便于蓄墨的汉笔特点,很适宜于在竹、木质地的简牍上书写。它的发现对研究我国汉代毛笔的制作水平以及演变过程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是武威汉代文化发达的重要标志和实物见证。 《仪礼》木简 5、《仪礼》木简 《仪礼》木简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城西南15公里的祁连山麓、杂木河西岸的磨嘴子的一座土洞墓中,当时发现一批《仪礼》简,共枚,字,这是自晋太康二年(公元年)汲家郡魏墓出土竹书以后,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量发现的经书。 《仪礼》木简用汉隶书写而成,笔势流畅,工整秀丽,是汉代墨写隶书的上品。简上隶书结体扁平,字距宽阔,疏密相间,极富节奏韵律,呈现出一种空远的意境之美。对研究隶书风格的发展演变和章法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仪礼》木简(局部) 这批汉简,除少数竹简以外,绝大部分是木简,用松木制成,每简长约50.5~56.5厘米,每简有字60个左右,都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上有削改和阅读的记号。据考证,这批简册在入葬以前不是为殉葬而写的,而是墓主人平时诵读的经书,其中一枚后有“河平口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解”一行。“河平”为西汉成帝年号,即公元前28~25年。这说明墓主人生活在成帝年间,可能是所谓文学弟子或文学弟子的老师。 铜车马出行仪仗俑(12套) 6、铜车马出行仪仗俑(12套) 这套仪仗俑出土于东汉武威雷台汉墓,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铜车马出行仪仗阵列,出土共计99件,由38匹铜马、一头铜牛、14辆铜车、17位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28个奴婢俑组成。 铜车马出行仪仗俑(12套)(局部) 轺车和斧车是仪仗队的前导车,是仪仗队中最重要的部分。轺车由车、伞、御奴组成。斧车由车、马、斧、御奴组成,车上立斧以示权威。 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数量最多、阵容与气势最壮观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铜车马铸造精湛,体现了汉代铜雕艺术的成就。 根据所出铜马、铜俑胸前所刻铭文“守张掖长张君”“冀张君小车马御奴一人”“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小车马御奴一人”等可知,雷台汉墓主人为一张姓将军,曾任张掖长,后又兼威武郡左骑千人官等。看着这组铜车马出行仪仗队,可以想见墓主人身前出行时的气派景象,彰显了汉廷在河西走廊地区的统治力,保障了丝绸之路的通畅。 “晋归义氐王”金印 7、“晋归义氐王”金印 印为金质,驼钮,印面正方形,印刻小篆印文“晋归义氐王”五字。这是西晋中央王朝赐给氐王的印信。汉晋时代,氐族散居於西北及四川地区,不同分支有青氐、白氐、蚺氐等“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归义”是中原朝廷对边藩归附行为的懿美。晋朝赐予氐族王印多铜质或鎏金,此印为金质,与内地诸侯王同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晋时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 “晋归义氐王”金印(印面)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陇南西和县相继出土了“魏归义氐王侯”“晋归义氐王”“晋归义羌侯”三枚金印,是氐、羌少数民族被纳入中央王朝统治的直接见证。 高善穆石造像塔 8、高善穆石造像塔 高善穆石造像塔,北凉承玄元年(公元年)酒泉市出土。高44.6厘米,为我国有纪年的早期佛塔的珍贵实物资料,是甘肃省博物馆国宝级文物。 高善穆石造像塔(局部) 高善穆石造像塔呈圆锥形,由宝盖、相轮、塔颈、塔肩、塔腹、及塔基组成。宝盖为扁平的半球形,塔颈周围浮雕八个方形柱,其上雕七重相轮。覆钵式塔肩周围并列凿八个园拱形浅龛,龛内分别高浮雕七佛与一弥勒菩萨像。佛面形圆润,肩宽体健,着通肩袈裟,上身微前倾,结跏趺坐、双手作禅定印,衣纹细密如行云流水,弥勒菩萨上身袒,下着裙,披巾绕臂下扬,交脚式坐,佛或菩萨古朴而庄重。圆柱形塔腹上阴刻《增一阿含经》中《结禁品》中的部分经文和发原文,上题“高善穆为父母报恩立此释迦文尼得道塔”。八面形塔基上每面阴刻一像,分别为四男四女,男像上身袒,带项圈,下着犊鼻裤,均有圆形头光。女像上着圆领对襟衫,下着曳地长裙,手捧花或珠宝。每身像左侧上方刻八卦符号,其排列与《说卦传》中的八卦方位顺序一致,八尊像分别依次代表着龙、树、狮、鸟、河、山、火、象、珠、风神等,这与当时盛行的鬼神护法思想有密切关系。 |